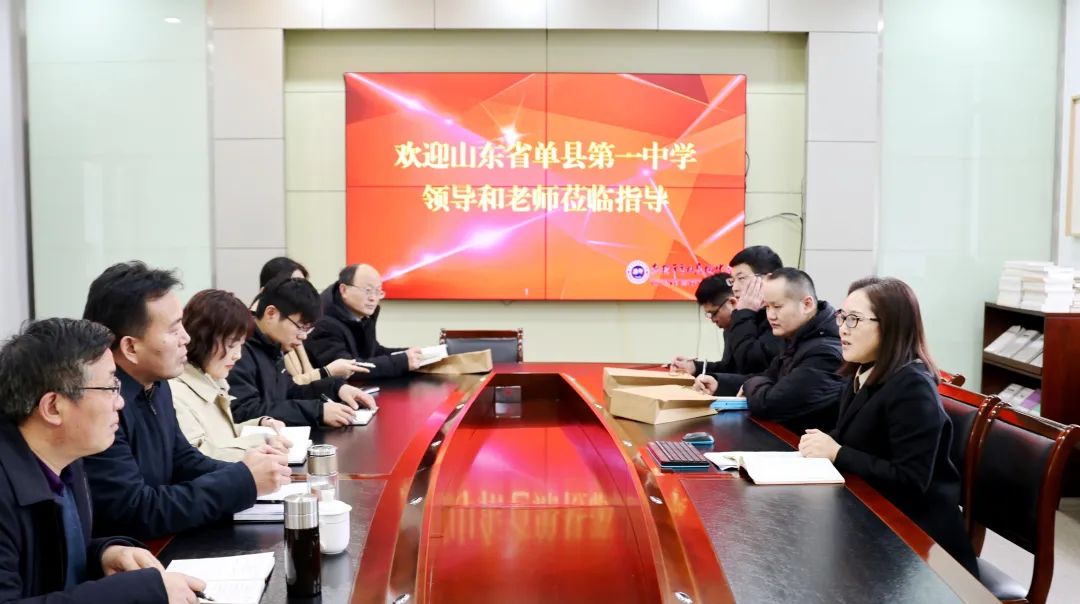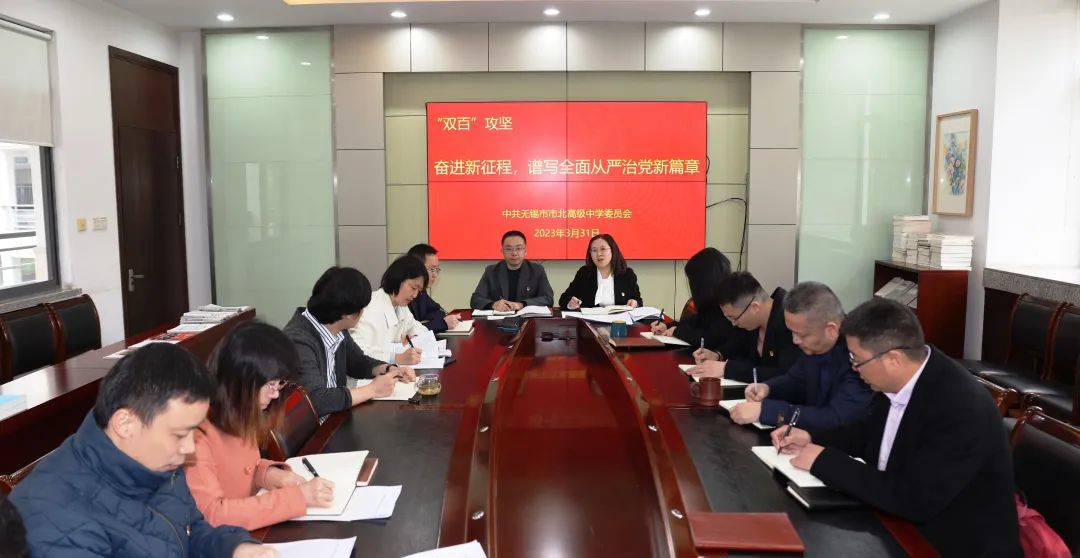学校概况
母校三春晖
学子寸草心
—贺母校无锡市北高级中学80周年校庆
寒来暑往、岁月如梭,蓦然回首:我们高中毕业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母校无锡市北高级中学即将迎来80周年大庆,追忆逝去的流金岁月,回忆母校的“城南旧事”,感恩母校和老师的培养,祝福母校兴旺发达,永远辉煌!
我是1956年进的初中,1962年高中毕业,同年考入了北京清华大学,在无锡市第四中学(无锡市北高级中学的前身)就读6个年头,这段时期是我们青少年重要的转型期,在这里我们增长知识、陶冶情操,那是充满着友情、温馨的摇篮 。
有同学这样说:有一段岁月,历经沧桑却依旧清晰可见,那就是我们中学的宝贵时光;有一个地方,阔别多年却依旧使人思念留恋,那就是我们的母校;有一批精英,时光远去,却依旧星光灿烂,那就是我们的老师。
对母校的回忆
无锡市四中的前身是私立原道中学,是一所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原道”取自唐代韩愈之的名篇《原道》,夫“道”者,世间万物运行之规律也,探索之,弘扬之,即知即行,是谓“原道”。(此解释摘自:叶圣善“为市北中学校训制铭”)
四中座落在小山里桥沿河的民主街上,门前有条小河,无锡有名的天主教堂紧靠四中,每当做礼拜时、颂经响起,在学校贴近教堂主建筑的地方尚听到教堂里回荡着的空灵和祥和的钟声。
四中校舍的部分原本属于天主教堂的建筑、呈欧式风格,砖木结构、上下两层。一楼是初中各班的教室,还有办公室、校长室,总务科等,各教室门前有西式拱券的走廊相连;二楼,木头地板,是实验室、图书馆以及单身教师的宿舍,从这座欧式建筑楼往东,有一排低矮的砖木结构平房,用作礼堂并兼作教工学生食堂,礼堂和欧式建筑楼之间有一片阔大的露天空地,可以容纳1500多人开会,每学期全校的开学典礼就在此地举行;从欧式建筑楼往西,陆续建了二幢二层的教学楼,先建的一幢外墙为石灰抹面、白色,另一幢则靠近大操场,外墙灰砖勾水泥缝、学校称“新楼”,58年因增设高中部才建造,看起来也较新、窗户也比其他教室大,高二、高三的教室安置在新楼。
欧式建筑楼和白楼之间、是一条东西走向、宽度不足三米的竹木结构的长长走廊,走廊的一边挂满了团委、学生会主办的黑板报和墙报,每每经过此地,我总要驻足留步,看看板报上别人写的美文,也顺便看自已投的稿子,自我欣赏。
2012年,我们高三(2)班同学曾相约进行了50周年聚会,并由胡海良、陈德兴、封锡英等同学组织编辑了一本纪念册子和一张光盘,记录了这次难忘的活动:那是一个多情的春天,樱花、桃花相继开了,同学们在无锡吟春苑相聚,是啊!江南的一抹雨烟迷蒙了凝思的双眼,尘封的往事拨动了思绪的琴弦,同学们记忆中的英俊俏丽已经不再,站在面前的是满头白发的老人,许多同学特地从外地赶来,这是毕业半个世纪以后高三(2)班同学的第一次重逢,老班长陈德兴动情地说:“忆往昔,三年的高中生活况如昨天,同窗情谊深如瀚海。”那时候,我们曾经那么青涩、纯真:什么都不懂,唯有求知的欲望,有时我们会仰望蓝天,看着飘动的白云,对未来充满幻想和憧憬;我们相信只要付出,定有回报,默默耕耘、奋力上进、天道酬勤;我们清澈透明,不讲谎言、讲究真诚,实实在在地评述那是一段不平常的流金岁月。
在中学学习的那个年代是充满激情、狂热的年代!大炼钢铁、除四害、大跃进、经济困难、阶级斗争无一例外把我们卷进了历史的旋涡:记得,我们曾站在屋顶上,敲锣打鼓、手展彩旗愚蠢地灭“四害”;记得,我们曾不止一次去锡惠公园工地劳动、建设映山湖;记得,学校曾要求我们回家砸锅卖铁、支援风风火火的小高炉;记得,经济困难、天灾人祸使师生一起面临长期的肌饿和挨冻;记得,因为阶级斗争、家庭出身,不少同学影响到升学、工作,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这些政治运动深刻地改变着同学家庭和他们自身的命运,记不清,我们走过多少曲折、崎岖的路,记不清,我们登过多少台阶、爬过多少坡,庆幸的是我们班的同学终于在艰难中走了过来,历史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困惑和迷茫,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被动地选择了不同的职业,大家为了祖国的发展和振兴,为了实现那个曾经有过的梦,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外云卷云舒,谈定面对着遇到的一切,我们这一代同学尽力了,我们把美好年华献给了那个时代。
对老师的感恩
有人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中学何偿不是如此,学校的好坏不是看校舍的高楼,而在于老师的素质。四中的老师与当时无锡所谓的名校老师相比较是属于最优秀的,他们博学多才、为人师表、敬业尽职、无私奉献。
我特别感恩以下几位老师。
初中二年级第二学期,在执教我们班的老师中来了一位英俊、帅气的语文老师,他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介绍自已:“我叫周建平,今天是生平第一次讲课,也是我第一次讲授语文课,要求你们课上必须用普通话提问、对答;课下也希望你们用普通话交谈,因为我听不懂你们的无锡话,建议你们每天跟中央人民广播台的播音员学、练,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周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曾任国务院的法语翻译,因当时众所周知的原因离开北京来锡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全校普通话讲得最纯正、最好的老师,其实不是北京人(即:“京片子”),而是宜兴人,他不仅能听懂无锡话,而且也会流利地讲述带点宜兴口音的无锡话。他用这种“倒逼法”逼我们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这种语言习惯使我收益非浅,考入清华大学后能很快地适应北京的语言环境,我哥哥就不同,虽然长期是中专老师,但只会用无锡话讲课,外地学生就有反映,虽然课讲得很好,但他们听不太懂,影响授课效果,影响彼此间的交流。
周老师才华横溢,他对鲁迅先生作品颇有研究,课上他讲的鲁迅生平,讲的鲁迅短篇小说《祝福》、《故乡》、《阿Q正传》等,我听了简直着了迷,有一次,他讲鲁迅在《祝福》中对鲁镇除夕的描绘,爆竹声声、音响的浓云、团团飞舞的雪花,用了诗一般的语言:“…我给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竹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灯光花,是四叔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时候。我在朦胧中,又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连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课后,我设法把文章整段背了下来。
每次他对作文批改得特别仔细,还要加上长长的批语,有时批语长度超过我的半篇作文,他还给大家开了课外阅读书单,在他启示下,我的课外阅读不再局限于《儒林外史》、《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国内名著了,《牛氓》、《高老头》、《茶花女》、《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飘》等外国名著也进入我的阅读计划,真的,在周老师的教导下,我的语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周老师博览群书,后来文化大革命以后落实政策,他重操旧业,回到翻译本行,也调出了四中,在无锡交际处当处长去了,以后凡是无锡重要的外事活动,他当首席翻译,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说:“太忙了、太累了,退休后,口译工作说什么也不想干了,闲来希望写点书。”可惜,他的这个“未来梦”终究未能实现,在即将退休前,他突发心肌梗塞,来不及抢救过早去世了,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充满着无尽的惆怅和悲哀!
我很庆幸,四中的语文课又来了个好老师,高一的语文课是王爱珍老师上的,她毕业于安徽合肥师范大学中文系,那年教我们时她的年龄大概三十几岁,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王老师穿着素色兰点的连衣裙,她的美丽、大方、亲和的教师形象,有点像当前经常在中央电视台露面的当红北师大教授于丹,王老师讲课特别认真,始终脸带笑容,常常声情并茂,加上良好的肢体语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讲解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轻飚杨柳直上重霄九。”引经句点,运用了几乎所有名人对这段诗词的全部诠述,其中有: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诗人藏克家、张光年、文学家何其芳等的不同解释,最后王老师说,她倾向于这种解释:杨柳轻飚是说扬花柳絮随着风儿飘荡,比喻为杨开慧、柳直荀两烈士的英灵升天了、飞得很高,直上九重天,王老师的点评大大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还有,她讲授作文喜欢选用同学写作文,我常有机会入选其中,当然兴趣很高,也高兴,所以我喜欢上她的课,王老师满怀热情地把知识传授给我们、也给了我们许多快乐。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始终微笑、始终给同学于快乐、乐观向上的年轻老师,她当时正面临着困境,她的爱人失业在家,必须帮他找工作,她的家就租住在我家附近,已经有了一个女儿,租赁的房屋很小很小,我们毕业后没几年、王老师调走了,她先调到了一中,后来又调到另一所技工学校,有一年,我和同班同学冯金华去看她,她说:“技校生只对车、铣、刨、磨等技术感兴趣、不想上语文课,与他们上课提不上劲儿。”一个好老师,没有发挥她应有的作用,委实太可惜了。
我还要提到我的高中班主任浦德坚老师,他的教师形象当然比不上周建平、王爱珍老师,但他的博学多才同样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浦老师教我们高中代数,他的教授方法很有特点,他的经验是:“定理、概念讲述清楚,”“难点要慢,慢才能懂,懂才是快,”“重点要重复、不厌其烦才能深刻,使学生终生难忘,”浦老师常常根据学生特点因材试教,所以同学感到上他的课就是轻松。他的黑板书写也有特点,一堂课,正好一个版面,不写写涂涂,准确到几乎每当课不用黑板擦。后来听说,我们毕业后学校要他改教英语,因为缺英语教师,浦老师答应了,他毕业于上海圣亚瀚大学,原来英语功底就比较扎实,浦老师是个教师中的多面手。
浦老师一直关心他执教过的每一位学生。离开四中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系,他关心我的大学分配,关心我以后工作的异地调动,待到应该谈婚论嫁的年龄,他关心我寻找的对象,结婚那一年他还赶来我家参加我们俭朴的婚礼。每年我们高三(2)班学生都要去看他,他能记得当时各位同学家长是干什么的,总要问问家搬到哪儿去了,父母亲还健在吗。
浦老师终身未成家,一直过着单身生活,他把所有精力全部用在他热爱的教育事业上了,他视学生为自己的儿女,关心学生学习、工作和生活,今年恩师浦老师已经九十三岁了,老年性心血管病、高血压正在折磨他,目前他正在住院治疗,上个月我们班上同学一起去看过他,希望大家都要关心他,但愿他能坚持住、挺过去,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我还要感谢在四中曾经教过我的所有老师,初中有:丁慧斐、缪公权、江文华、曹润、李馨、陶豪伦、刘厚江、李良干、吴志强、章学政、吴金荣、时有经、陈科、苏式等老师;高中有:张全林、韦维琴、陆印吾、潘人俊、孙国清、章舒人、陈冀亮、过菊森、王禹忱、薛剑等老师,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每一位优秀的师德、教书育人的功绩。
值此母校无锡市北高级中学建校80周年之际,祝福母校有更大发展,再创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