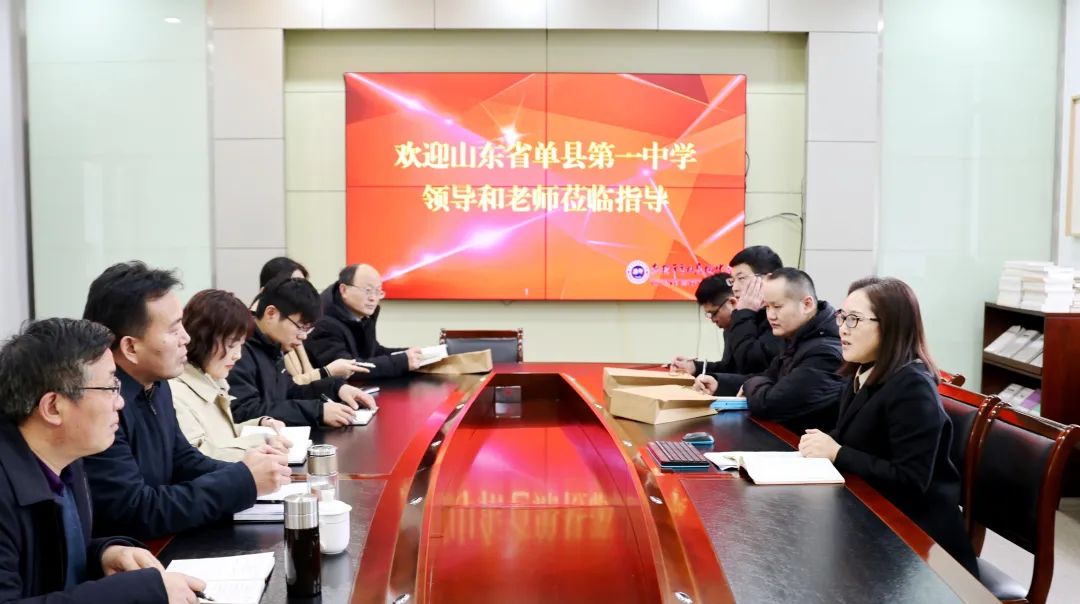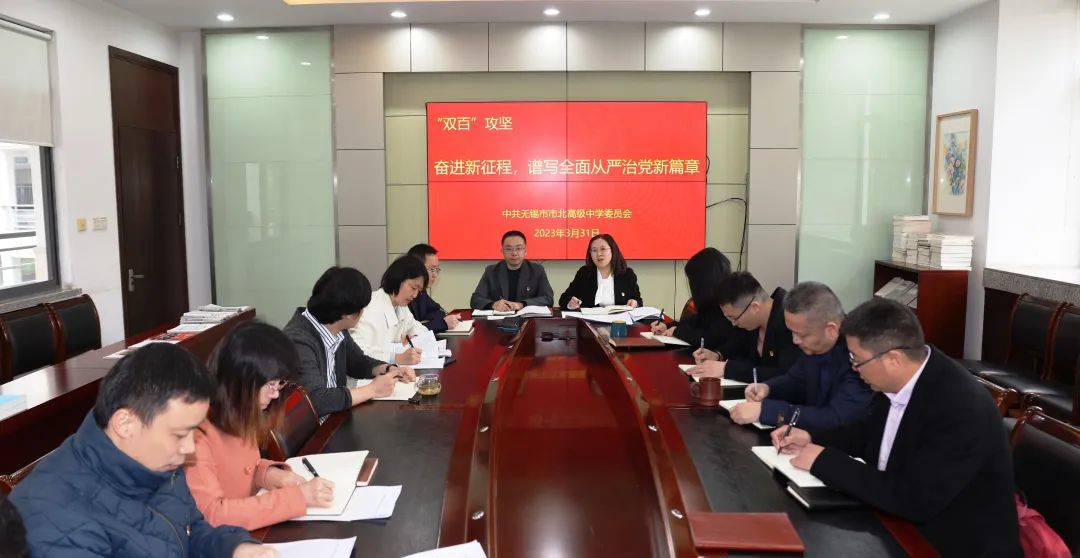学校概况
往事如烟
1960年在一中初中毕业,想考南京建工,结果分到了四中,高一2班,班主任姓张,教化学,带全班去农村劳动,那片农田就在现在的沪宁城际铁路旁,现在已是一住宅区了。当时班上同学的年龄分布相差达10岁,几个年小的只有14岁,现在来讲应属童工,收工回校路上,一个班干部走到班主任旁,欲说还休、吞吞吐吐的样子,说“某同学,砍一棵草,18刀,还没砍下来。”班主任回了一句“数18刀时你在干什么?”,那个打小报告的碰了一鼻子灰。差不多54年了,至今还记得。
当时的高一2班有50多人,到高二时(61年)只剩20多人了,维持了半年,高二下学期就一分为二,分别并入一、四班。
高一的语文老师姓高,记得61年,看过学校工会给他办的退休证书。他课外给我讲陆游的诗选,第一首是:陆游的《新夏感事》
百花过尽绿阴成,漠漠炉香睡晚晴。
病起兼旬疏把酒,山深四月始闻莺。
近传下诏通言路,已卜余年见太平。
圣主不忘初政美,小儒唯有涕纵横。
公元1163年39岁的陆游,听说宋孝宗即位之初下诏广开言路,流泪预测来年天下平安。
可见古人把“广开言路”与“天下和谐”互为因果。
左流横行时,50年代向前苏联一边倒,学校外语只开俄语。60年开始设英语课,当年的新生,1、2班是英语,3、4班是俄语。我们2班的英语老师是张大川先生。据说他原来是教数学的,可能当时英语缺师资,才改科的。我看过他的备课本,有边复习边教的痕迹,他的板书很漂亮,开学没多日,他上公开课,那时的英语课本开始就是“Long live xxx”,后面有“我是、你是、他是、她是”等,记得张老师叫我起來说“我是…”,我一紧张,脑中只有中文的“是”,结果说成“I is…”,他无奈叫我坐下。多年后我才知道,一堂公开课对一个老师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却被我搞砸了,至今深感内疚。
1962年下半年,高三4班,语文老师是瞿文渊先生,有次,瞿老师在我的一篇作文上的一大段批了许多字,有“用词不当、语法错误、…”等等,全是批评的话。在他教我的一年中就这一次。
那次我是偷懶,从报纸上抄了一大段来凑字数,抄的是当时刚开过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后来据说那是胡乔木起的稿。而老师批的恰恰是这一段,而且批得很有道理。虽说胡对钱钟书、杨絳不错,但其本性上是个左棍。那作文本我一直保存到66年,文革开始,我就把它烧了。
高二下学期拆分到4班,教语文的是班主任戴老师。他那时年纪轻,上课时会背一些宋词,如辛弃疾的《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如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他还谈起过李希凡、蓝翎。
我对李、蓝两人看法的改变是在1968年底。当时被暂时安排在周扬家乡一个瓷厂的职工宿舍里,一座建在一小山丘上的统子楼,砖木结构,不久前曾经历过武斗,留有火烧过的痕迹。了解楼房环境时在一垃圾堆里拾到两本书,其中之一是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没有封面,原样保存至今。看了那本书才知道俞先生了不起。李、蓝马仔而已,后来李官运亨通,蓝翎却被打成右派。
上学期间最不爱的课是政治,但是至今不忘的是第一个政治老师,姓胡,一位男青年。1957年反右时正在无锡市一中上初中,新开了政治课,胡老师用批判知识分子修身养性的形式详细介绍、解释了三句话,<独善其身>、<能忍自安>、<知足长乐>。这三句话五十多年来始终不忘,也明白老师在那个年代的用心良苦。高一时,政治老师是个女的。当时我坐在第一排第三列,同桌是杨汝勤。老师上课时与别的老师不一样,经常会嘴里含着一粒硬糖进教室,因为我坐得近所以能看出来。她还有一习惯,就是讲话中经常会带进“怎么啦!”,就象口头禅,无锡话称为“话搭头”。讲的内容听不进,为了度过那枯燥的45分钟,几个同学就给她的“怎么啦!”计数,下课后就互相核对,这节课有多少个“怎么啦!”。现在反思,真是很对她不住,不但她讲的内容不记得,连她的姓都忘了。高三时是班主任过老师讲课,讲的是哲学。虽然当时四人帮及其后台还处在阴谋策划时期,但学校已不可能用冯友兰教授书中的内容,只能是那个“矛盾论、实践论”,还有一些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内容。
1963年4月30日,班上同学相约五一游蠡园、鼋头渚。当晚狂风暴雨,早晨雨仍很大。我和范崇乐骑自行车,从人民桥(当时习惯称西门桥,即原无锡县城的西水关)经通德桥、中桥,到蠡园。衣服湿透了。门票是5分钱,进园见班上同学到了不少,他(她)们是乘1路车。那天的蠡园就好像我们63届高三4班的包场。去鼋头渚时雨小了,面对蒙蒙细雨中的太湖,那种难以描述的情感人生中就这一次。现在那里不但门票上百,进去后的主要活动是如何避免碰撞于人流之中。
下午,雨停,我和范兄过长桥后左拐沿湖去梅园,经小箕山时,看到门口小桥没人,就想进去看看。(1953年前,上海回乡的亲戚摇条船能从湖区进入小箕山,后来就只能前苏联的人和官员能进了)。我俩才到桥上,前面就突然出现了个人,态度很好,告诉我们这里不能进,其实我们也只是去试试,因为当时无锡民间流传彭元帅软禁在里面。退到路上回看,发现水边芦苇丛中站着若干人。
范崇丹、范崇乐是亲兄弟,一班两兄弟的情况学校史上可能不多。前几天与崇乐兄家中通话,得知他身体尚未康复,记述作为挂念。
那时学校里流传过一事:教我班几何的孙老师,某次游蠡园,远见一人,象是周总理,想走近时即被拦截,回校后有关部门已在等侯找他了解情况。记忆中孙老师就住在学校附近。后来看过一资料,在那个时间段,周总理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病休确曾到过苏、锡。那时数学分几门,代数、平面几何、三角、立体几何。教三角的老师年龄已很大了,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现在还有他在讲台上用单位圆证明 [sin(α+β)=sinαcosβ+cosαsinβ]的印象。有一次冬天,冷空气袭击无锡,早晨第一节课是三角,但老师没来教室,等了一会才被告知他年老体弱,冻得起不了床。可见当时的教工宿舍条件并不好。
1972年,所在厂招工农兵大学生,为报考的青工复习的人员由厂政工科审查指定。我同宿舍的一位搞测绘的中年技术员给青工复习数学,一次看到青工的记录本上居然是[sin(α+β)=sinα+sinβ],大愕。
高三时,1、2班的物理老师姓杨,听62届的学长说过,杨老师曾预测62年的高考试卷内容,出现了失誤。63年他转为预测数学,当时1班的同学告诉我杨老师说:要用到对数表的数学题是不会考的。他讲得是有道理的,不知现在高中教材的情况如何,在六十年代,高中的教材中会有一本“四位数学用表”与课本一起发。内容有角度的正弦、正切值,常用对数和反对数。教材不能带进考场因此得出这个预测。
63年的高考数学试卷中恰恰有这一计算题,卷中列出了计算中要用的三列数据,既含有对数又含有反对数。题目并不难,就是考核基本概念“对数的尾数不能是负数,如果计算中出现负数,就在首数中加—1,把尾数转化成正数。”
“四位数学用表”只有十几页,在七十年代初,曾用过一“六位数学用表”,里面还含自然对数,多了两位有效数就有《辞海》的缩印本那么厚。
1960年是近代饥饿最严重的时期,民主街学校在黄巷有一农业基地。我们去劳动时有一专职的老师安排工作,看样子他与当地的农民关系很好。听年龄较大的同学谈起,他家庭困难,有时会拣别人扔弃的食物处理后使用,谓之“臭鱼不臭味”。高二时在一学校工会活动室见过他,躺在床上,请我帮他拿一东西,说“我这病不会好了,但你放心,它不会传染。”
坦然面对生死,现在我们这些70左右的人能做到吗!
1960年的高一2班,同学年龄差有十岁,小的14岁,大的有20多。年龄小的有几个喜欢玩弹弓,常带到学校,课间就会拿出来拉几下,就象玩拉力器。他们初中时碰上除四害,那弹弓就是麻雀杀手。当时打麻雀有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人,每人每天要交多少双麻雀的脚爪。到后来只要是鸟脚爪就行,所以许多燕子一类的益鸟也跟着遭殃。58年底真是个千山鸟飞绝。59年虫灾非常厉害。
弹弓用的弹药有几种,最简单的是小石子,还有自制的泥丸,用惠山泥人的原料做的属上品。也有个别的用轴承钢珠。
记得有天到校,见班上有几人神色奇怪,后得知,昨晚他们去锡惠公园玩,见远处一原初中的老师与其女朋友,可能想开个玩笑,一弹弓过去,不想打在老师的脸上。隔天见那老师脸上还有伤,记忆中该老师是负责校团委的。